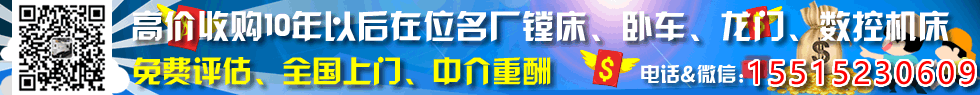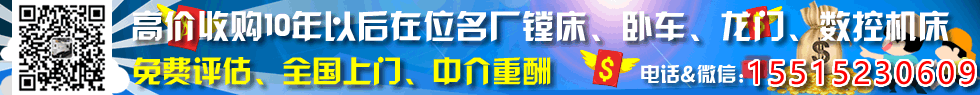【编者说】我们今天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特点,或是什么中国模式,更不存在什么中国震动,而是正在重复当年亚洲四小龙的老路。 从20世纪60年代开端,韩国、新加坡、、香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我们今天很多人吹捧的中国模式就是抄袭这个而来的
一、日本道路vs香港道路
我先读几个数字给大家听听: GDP一直在双位数增长,除了短期的波动,几乎每年保持GDP增长率超过10% 出口扩大迅速。 十年之间,各个地区的出口都是之前的十倍以上 GDP里面工业比重将近一半,消费比重一直不高 工资开端一直不怎么上涨,但是出口导向型搞了十年之后,劳动力忽然全面缺乏,工资大幅上涨,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端抬头 好的,大家必定会感到我是在说中国经济。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是亚洲四小龙在出口导向型模式后期的真实写照。 甚至顺着这个思路你比较一下会创造我们今天的发展速度其实还不如人家四小龙当年搞出口导向型的程度呢!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 而我们的出口导向型重镇的苏州,外贸进出口总值不过是十的12倍。 201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是1.6万亿美元,不过是2001年的出口总额(2662亿美元)的6倍。 但是,工资快速上涨很快让四小龙的经济走向了经济分岔路。 一条路是韩国、、新加坡走的路,其实就是和日本一样的道路,另一条路就是香港。 从一开端,香港就比其他地区都荣幸,因为从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始终有大批从内地偷渡进入的劳动力,这样香港一开端的工资上涨压力就不如日本那么大。 在60年代,香港的纺织工人平均每年工资上涨幅度是5.6%,十年下来是之前的两倍左右,但是在日本,社会工资总额累计增长245%,各行业人均现金收入由1.85万日元/月增至4.89万日元/月,名义累计增幅164.3%,远高于GDP增长的幅度。 可以说,香港这段时间很像我们过去十年的东部沿海地区,因为一直有中西部的便宜充裕劳动力补充,所以工资上涨幅度不大。 但是这反过来决定了两条道路截然不同的命运。 从1965年到1980年,香港的经济命根子都是纺织成衣产业,而机械、造船、电子产业都没有发展起来。 与之完整不同的是,韩国、及新加坡都步日本后尘,由劳动密集为主的纺织服饰转变为电机机械设备为主的技巧密集工业国家。 与此相反,韩国比较倒霉,本来在1970年纺织服饰在韩国出口额的比重比香港还高,韩国事44.3%,香港是41.1%。 进入80年代后,韩国出口面临三大寻衅:发达国家的贸易掩护主义高涨;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差距缩小。 因此,韩国政府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巧升级,形成出口主力产业。 同时对精致化工、精密仪器、盘算机、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战略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并将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积极发展的产业。 冶金机械电子这些资本技巧密集型工业占总出口比值由70年代的7.2%,90年代上升为35.5%,2005年甚至更成长至69%。 纺织服饰业成长大幅降落,纺织服饰的占出口比值从1970年的44.3%,降落到2005年的4.56%。 二、日韩如何应对工资上涨?
在正常的经济体,工资上涨本来就不是坏事。 首先,日韩的工资上涨机理和我们完整不同,我们过去对工资完整是压抑的,缺乏健全的工会制度掩护工人的利益诉求,现在又因为涌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租金上涨,所以倒逼工资不得不上涨,实际上,我们只是名义工资在上涨,实际可安排收入在降落,前者让企业苦楚,后者让老百姓受难。 与此相反的是,日本工资上涨之后,成果只是内需更强了,实行“收入倍增打算”后,1973年日本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按现价美元盘算)为49%,比1970年上升1个百分点,到1982年达到55%,比1970年上升7个百分点。 因此,工资上涨本身并不是个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日本从来没在腾飞期把工资当个问题来面对,日本政府面对的问题重要是汇率和通货膨胀,而日本的政策目标就是让老百姓的工资翻番。 日本企业反而是有意把用工较多而产值较低的一些产业转移到东南亚、韩国和去。 其次,只要你的教导系统和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工资上涨能增进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消费型经济,但是,我们国家的教导系统是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根本无法勉励顺利的经济转型。 举例来说,日本的电池产业应对工人工资大幅上涨之路是搞全主动生产线,但是,中国呢?你想贷款,政府信贷调控,你买设备还得交17%的,根本没法抵扣,换句说,还没开工呢,就得先交税,搞不好政府还给你搞个拉闸限电。 所以,中国企业最弹性的解决措施是半主动生产线,资本投入小,随时开工,随时加班,随时休班。 再比如说,韩国选择的前途之一是扶植游戏和数字内容产业。 韩国人的逻辑很简略,这个产业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在地理上毫无穷制,且市场潜力宏大,非常合适韩国的特点。 目前,韩国数字内容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第一大产业。 好吧,类似的事情在中国也不是没有,比如电动车,我们国资委也有16亿元资金直接支撑,不过,只支撑16家央企,包含中国一汽、东风汽车、长安汽车、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国保利等。 民营企业不管你实力如何,全部被排除在外,不能参加这个电动车产业联盟,我最好奇的是,你搞电动车,为什么这16家央企里一家做电池的都没有呢? 此外,韩国政府建立了造就数字内容专业人才的较为完整的教导系统,包含从职业教导到大学教导等各个教导层次。 游戏相干教导机构共有84家,研究生院8个,大学5个;私立教导机构22个,高中3个。 通过官方机构向韩国的游戏企业尤其是小型游戏企业供给人员培训,调查行业人才供需状态,供给培训课程,增进学术交换;对从事游戏产业的高技巧人才免除两年兵役等等。 我们再想想今天中国的教导系统呢?连一套公平透明的研究经费拨款系统都还没建立起来呢,何谈造就创新人才? 三、香港道路的终点:
那么,是什么打垮了香港企业家?很简略,就是!香港企业因为有这个腹地,所以就不思进取,直接把工厂转移到内地,与此同时,香港又推行了毛病的政策,孕育了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这样,香港企业透过制作业积累起来的资本并不像投入了IT产业,日本韩国投入了半导体产业和造船这些技巧密集型产业。 等到亚洲金融危机,股市和楼市泡沫崩溃,香港透过出口导向型积累起来的这些财富刹那间付之东流。 20世纪90年代前7年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一共为香港带来约7万亿港元的‘财富增长’,相当于香港在这7年间GDP的总和。 也就是说,1997年以前社会所有的财富都被股市和楼市的泡沫吸走了。 在金融风暴的激烈冲击下,香港经济泡沫应声而破,房地产价格急速回落,社会财富大批萎缩,香港由此进入经济的衰落期。 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年底,5年的时间里香港房地产和股市总市值共丧失约8万亿港元,比同期香港生产创造的本地生产总值还要多,也超过19977年吸进股市和楼市的7万亿港元。 实际给老百姓直接造成的冲击比这些宏观数据更为残暴。 1997年,香港楼市的重要指数“中原城市指数”高踞107的峰值。 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中原指数最低跌至30点,楼价急挫60%-70%。 无数通过借贷置业的业主,瞬间变成“负资产”,无数炒楼客破产。 到了2003年6月底,香港大约有10.6万宗负资产者申请破产,占所有按揭的22%。 换句说,五分之一的香港有房族实际上都破产了 欢迎关注微信“东方知行社
”,豆瓣小站“东方知行社
”,新浪微博“东方知行
”,就有好书相送
!
相干著作推荐:
《是最大政策
》 《优雅的理性
》(
任志强可以野心优雅,但经济学应寻求一种优雅的理性,与齐名的熊秉元,带您在生活中学习经济学)
《郎咸平说:让人头疼的热门》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这是一个经济热门频发之年。 郎咸平说,“头疼医头”头更疼,需要大手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