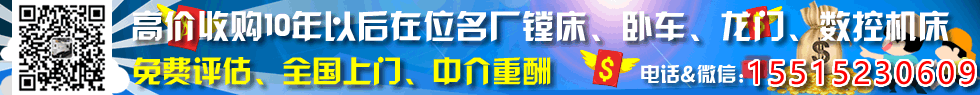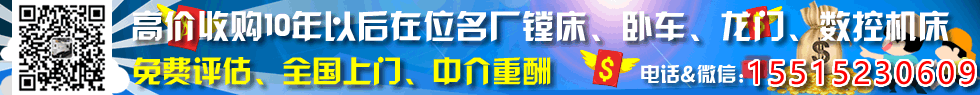沈阳机床厂区 置之逝世地而后生是中国企业创新路上的主旋律,变更的中国转变了这些企业的环境,迎难而上的这些企业又转变了中国的面貌。 记者刘洋 初春的沈阳依然寒冷。 每天早上,阳光尚未来得及温暖料峭的空气,170辆班车就已经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启动,其站点之密集甚至可与这座城市的公交系统相媲美。 这些班车的任务是将14000名工人送到位于城西的经济技巧开发区——沈阳机床团体的总部就在那里。 就像很多人无法懂得沈阳人痴迷的“二人转”中的风趣,躲在消费品后面的人通常也都无法懂得沈阳人对机床和制作业的情绪。 这种情绪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新中国首个五年打算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辽宁承建了24个,其中的沈阳第一机床厂、中捷友谊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更曾跻身“十八罗汉机床厂”之列。 1993年,这三家机床厂和辽宁精密仪器厂合并为沈阳机床团体。 从那时起,沈阳人就对自身在机床产业中的重要性深信不疑。 我们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端 中国的创新故事 光辉岁月有时会变成宏大累赘。 2004年,沈阳机床参加芝加哥国际机床展,成果因产品程度不够,而被主办方安排在地下室。 而后,沈阳机床的参观学习恳求又被当时最大的机床制作商德马吉拒绝。 再之后,沈阳机床试图通过合作来学习技巧的努力,再遭欧洲同行拒绝。 如果联想到沈阳机床在此期间的高歌猛进,这种苦楚就会显得更加莫名和激烈。 那段时间其实是中国机床工业的黄金时代,沈阳机床更是其中的翘楚:中国在2002年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时,沈阳机床的营业收入不过13.53亿元;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经历史性地达到120.62亿元。 问题的要害是利润:从2002年的458万元猛增至2006年的1.33亿元后,沈阳机床的净利润一直在急速下滑。 到2009年,其全年净利润只有2704万元,如果扣除债务重组和政府补贴,其净利润甚至已经为负。 其实,自2002年以来的8年中,沈阳机床即便在最好的年份也没能实现过3%以上的净利率,财务报表的失衡绝非偶然。 这时的沈阳机床似乎走上了中国企业习惯的路径:突然释放的市场刺激企业走向扩大,高速扩大引发的利润降落及创新乏力又令企业陷入困境。 沈阳机床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失衡,它也曾尝试通过其他方法扭转局面,其中甚至不乏激进之举。 他们曾尝试将4家主机企业重组为11个主机事业部,但这场“将几十年积累形成的结构系统和业务流程统统打破”的变更问题重重。 所以,当上级部门盼望沈阳机床在数控机床领域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时,这种远大的理想很快在沈阳机床内部达成共鸣。 对那时的沈阳机床而言,与其说这是一项不容有失的任务,不如说是求生的本能刚好与国家期望产生了微妙共鸣。 这是范例的中国创新故事 当中国企业因为国外对手的技巧优势而面临淘汰的风险时,他们总能在国家支撑下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这中间掺杂的复杂情绪又使这些企业的具有宏大的象征意义——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该地区其他企业能否走上以求发展的道路。 对这些领导地区浪潮的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只有一个——在所有可能路径中做出选择。 这并非一个简略的任务,因为创新过程的坎坷和平坦都不是清楚绝对的概念:今天省下的工夫可能需要明天付出更多努力才干补充;一旦通过走上创新道路,过往很多努力又会显得物超所值。 但在危机只是隐约浮现之时就大刀阔斧地,确实是个艰巨的决定。 一场堪比豪赌的变更 人们在创新路径上的不同选择,可以反响出看待未来的不同态度,“如果要在短期内解决某些急切的现实问题,借助外部力量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吸收《环球科学》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表现,“但创新其实是华山一条路,走捷径未必是好事情。 如果要造就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就必须依附自身力量摸索路径、积累经验和汲取教训。 ” 同很多人想象不同,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创新故事,这些故事蕴含的发展智慧也足够精彩。 但依附自身攻关的难度确实太大,因为这与中国企业传统的发展路径完整不同:巨额投入换来的不是高楼大厦和现代厂房,几百人在俏丽的写字楼里消费数年时间写写停停换来的只是一张光盘和记载在上面的几十万行代码,所谓的进步可能明天就会被完整颠覆,并让一切推倒重来,就这样还要不时面对人员缺乏和资金不足的考验,这个过是有点虚幻。 荣幸的是,对于沈阳机床而言,这场变更的领导者——团体董事长关锡友并不缺乏类似经验:2001年,他带领中捷友谊厂成功中标上海磁悬浮轨道加工设备项目,仅用6个月就完成了这项被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成绩至今仍不时受到业界赞美。 更荣幸的是,沈阳机床对也不陌生。 1991年,世界银行决定供给1.75亿美元贷款赞助沈阳传统机床业,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项目。 但按照当时惯例,世界银行的工业贷款一般不扶持国有企业。 为此,沈阳机床工业仅用10个月就完成了定向募集内部职工股票,又只用3天时间就取消了原有4家企业的法人地位,新的沈阳机床正是由此而来。 关锡友将突破点选在数控机床 数控机床是制作业的工作母机,也是工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标记。 而数控系统是数控机床的大脑,其成本占数控机床总成本的40%~50%。 沈阳机床想过从国外引进数控系统,但6000万欧元的高价和高昂的学习成本让他们望而却步。 这不仅仅事关几十万行代码——在几年的学习时间和可贵的创新经验面前,这些今天看来价格不菲的代码甚至不值一提。 那些与数控机床有关的运动把持、数学模型和运作参数看似简略,但其背后是一家企业日渐成熟的研发系统和工作理念。 更重要的是,由研发成功获得的信心会让企业走上以研发求生存的路径,这对企业永续发展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意义。 沈阳机床最终决定自主研发 当时,我国所产数控机床中经济型、中档与高级的数量之比约为70:29:1,这一比例在日本、美国分辨为0:80:20和0:60:40,关锡友自负可以通过“豪赌”抢得一块市场,这种自负源于两个断定:全球机床产业正加速向中国转移;短期内涌现性变更的可能性不大。 重要厂商的同质化竞争意味着,后来者可以有充分的市场空间,沈阳机床需要抓住机会完成转型。 为实现逆转,各种经济资源必须向研发倾斜 关锡友外包了部分机床生产,以保证有充分资源支撑研发;为了让不愿来沈阳的人才干为沈阳机床工作,他又在同济大学设立了上海分公司专攻数控系统;多次资金困境和人才瓶颈也被一一克服,当时,沈阳机床保持每年投入至少两亿元支撑核心技巧团队的研发运动。 筚路蓝缕4年后,名为“飞扬”的数控系统竟然真的在沈阳机床出身了。 要知道,只是看懂国外系统当初就被认为需要5年时间 瓶颈的突破刺激了关锡友,他很快调剂了目标,新的目标将2015年的销售收入上调至500亿元。 沈阳机床的员工将其描写为一个异常远大的理想,而理想的突破点就是加速数控机床的后续研发。 巨大的愿景总能驯服很多人,李宇鹏就是其中之一,领导着400人团队的李宇鹏是当前中国机床行业中唯一一个女性总工程师。 只是起点 李宇鹏是机床行业难得的复合型人才。 她有力学背景,又在科技行业供职多年;她熟悉国情,又有先进的管理经验。 在英特尔期间,她曾领导十余项重要产品开发,她提出的优化接口触点与中心处理器触点有效接触的方案,曾在2008年为英特尔创造了26亿美元的价值。 “在现在的中国,外企、国企和民企就像三个封闭的圈子。 人才在圈内交换很多,但在圈子间流动很少,”薛澜认为,“这也阐明我们对创新的支撑机制、对人才的勉励机制都还有待完善,人才竞争才是最重要的成果。 ” 李宇鹏很快证实了这些断定 首次见面后不久,李宇鹏就告诉关锡友,研发与市场不能相隔太远,研发前要与市场互动以断定新产品的边界条件,研究人员要学会做行业研究。 “最好的技巧并不必定比最简略的方案高超,因为不是所有行业都迷恋尖端技巧。 精度对军工航天很重要,汽车和消费电子更关注的却是效率,”吸收《环球科学》采访时,李宇鹏表现,“企业不能因为寻求高新技巧而疏忽市场,毕竟满足现实需求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关锡友交给李宇鹏的任务则是变更公司的科研机制。 像历史上每次一样,转变研发习惯和思维方法从来都不简略:研究人员已经习惯了设计最具通用性的产品,客户需求的个性化并不必定能够推动公司研发习惯的变更。 但李宇鹏通过引入项目制大刀阔斧地了上海分公司和沈阳设计院,这样员工就能以更高的积极性去懂得市场动态并推动技巧变更。 这次至关重要 沈阳机床盼望先进机床的操作不再是普通工人的门槛,这就请求智能技巧的运用必须能让机床操作更加简略;沈阳机床盼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大批采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请求最新的车间智能系统必须能让管理者知道车床的工作状态;沈阳机床还盼望能够在机床行业率先开展租赁业务,这又请求基于物联网的新型平台能容许机床应用者远程把持并实时知道机床工作状态,因为只有这样租赁双方才干实现信息透明和对称,才干戒备租赁过程中的风险。 李宇鹏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充满信心,因为人才正不断凑集而来,她甚至已经把上海分公司从同济大学的教学楼搬到了更加正规的写字楼里,因为这样“至少看起来像为IT人筹备的办公室”。 现在,上海分公司已经拥有员工130多人,这个数字在两还只有70。 每天,李宇鹏紧张地和谐着两地的工作,正在进行的60多个项目不容许这个团队的运作有任何差池。 “压力当然有,”李宇鹏说,“但适当的压力会让人成长。 ”李宇鹏对压力也有应对之道:她爱好睡觉,因为“睡梦也许会带来意外之喜”;也爱好在下班后散步,因为这样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最美好的时间:那时,落日照射沈阳,班车把工人送出厂房。 与李宇鹏一样,这些工人也对未来充满盼望:他们盼望2015年的目标能够实现,也盼望新厂区周边小区不断,这样他们就不需要每日奔走,就能有一些闲逸的欢乐。 [责任编辑:吴劲珉] |